每日經濟新聞 2022-05-29 22:54:24
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特別是在城市面對新一輪治理難題的當下,我們不妨回過頭重讀列斐伏爾,跟隨他“尋找”的過程,也為城市尋找新的解題思路。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501422272
今天是城市進化論的第1984條推文,我們決定推出“城讀”欄目。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的說法: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與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來將決定人類的未來。
無論是回顧世界城市化進程還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城市不斷進化、走向進步的來龍去脈。
今年是城市進化論團隊成立的第五年,一路走來,我們所做的正是見證和記錄這場前所未有的城市進化歷程,傳遞和匯聚推動這場城市進化歷程的那些最有價值的思想和聲音。
在日常推文的過程中,經常有朋友詢問城叔在看什么書,不妨借此把近期讀過的好書和閱讀感受整理出來,同時我們也推出“領讀計劃”,邀請大家在評論區和我們分享閱讀。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個體身處其中,不可避免遭受影響。書籍是人類的編年史,它將整個人類積累的無數豐富經驗,世世代代傳下去。
每當變幻時,不如去讀書。
疫情尚未過去。在“防疫情、穩發展”的“兩難”困境中,城市對更好治理模式的探尋未曾止步。
一種討論聚焦于基層治理模式上。有聲音指出,一些城市,管控小區的人員、物資進出由居委會占主導“把守”,傳統的“管理”思維一度造成倒賣物資、對居民采買物資不合理設限等“失控”狀況,大大增加了本就在隔離中居民的生活成本;而那些更具“用戶思維”的城市,發揮居民自治的力量,小區僅提供必要“服務”,反而讓城市面對疫情更有效率。
凡此種種,疫情之下城市治理方式的差異顯現。而在其背后,則是一個更加久遠的問題: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問題,城市應怎樣發揮其愈加重要的作用?
1970年,法國著名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在對“反城市主義”思潮的關注下,寫出《都市革命》一書。反思此前的城市理論,列斐伏爾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都市觀”——以“都市總問題式”(Problematique urbaine)的方式來重構都市認知和實踐,城市的集中性和復雜性成為核心議題,工業邏輯由此被都市邏輯所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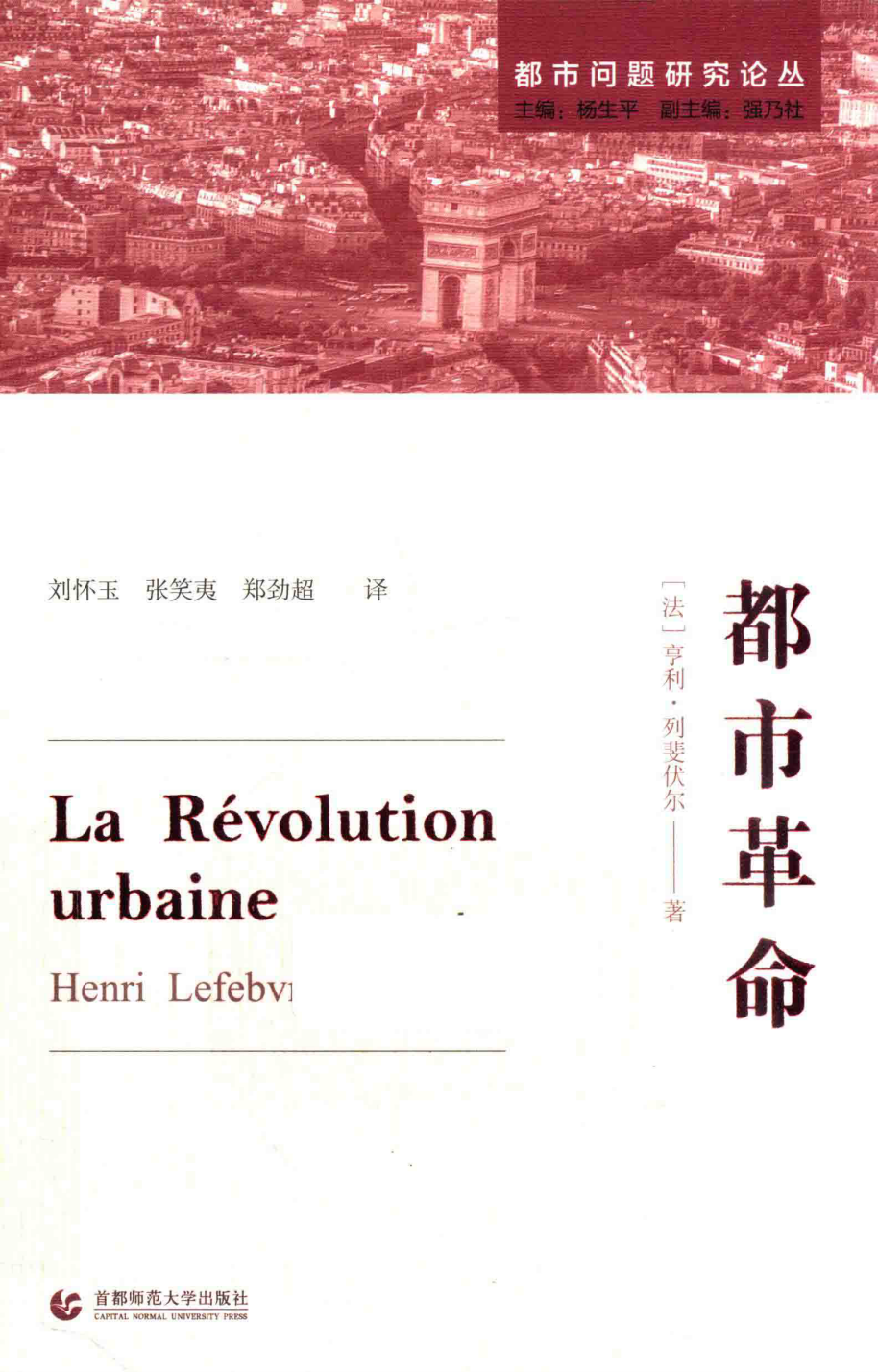
基于此,他呼喚一種對現有城市治理方式的“顛覆性”思考。站在都市視角反觀現有城市發展脈絡,他發現“規則化”“統一化”的治理方式成為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特別是在城市面對新一輪治理難題的當下,我們不妨回過頭重讀列斐伏爾,跟隨他“尋找”的過程,也為城市尋找新的解題思路。
如果反思現代城市的各個環節,兩種聲音一直貫穿始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這兩種治理模式總是相伴出現,跟隨其后的則是兩方支持者的慷慨陳詞。雙方各執一詞,城市則扮演一個治理方式的辯論場。
城市為何是這個模樣?或者根據列斐伏爾的提問,城市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模樣?
列斐伏爾曾梳理城市的變遷過程。最早,城市總是伴隨著農村出現,耕地、農村以及農村文化慢慢分泌出都市的現實。此時,城市(或者城邦)是一種國家的原始形態,它通常以“政治城市”的狀態出現,城市是封閉且割裂的。隨后,商業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現狀,交換和流動催生“商業城市”的出現。
在此之前,在和自然幾乎對立之下,城市的形態都比較單純,功能也相對簡單。工業資本及工業城市的出現顛覆了一切。按列斐伏爾的話說,在此階段,“工業所代表的非城市和反城市力量征服城市,滲透到城市之中并使之爆裂,因此使城市無限展開而走向社會的都市化”。這被他借用核物理學名詞稱為“內爆-外爆”的過程,讓都市走向“碎片化”。
現代都市的復雜性幾乎在極短時間內被裂變出來。
列斐伏爾反復強調復雜性對都市概念的重要性。從概念上看,都市實現了人、活動、財富、物質以及對象、方法和思維方式等各式各樣的集中化,市郊、郊區、二手房、衛星城等新造詞層出不窮。工業帶來的經濟增長,推動都市現象“沖破邊界”,令城市成為一個“大熔爐”。
但問題也由此產生。
工業城市的出現,伴隨著工業領域替代自然的過程。列斐伏爾提到,在理性、法律、權威、技術、國家和掌管統治權力的階級等名義下,自然被有條不紊、系統地強加上同質性的特征。更可怕的是,“一項總是重復進行但從未完成的工作,使工業分工的效率擴展至勞動的社會分工”,社會實踐的普遍組織結構由秩序和強制所構建起來。
工業的“一致性”和都市的“復雜性”之間存在一種“斷裂”。列斐伏爾用“盲域”加以總結,即一種無法以工業化邏輯來認識都市化現象的狀態。都市因而處于一種“未完成”的狀態當中。
“都市被簡化還原為工業”,都市的日常性特征被蒙蔽,并“受制于企業需要并按企業理性來對待”——這也造成了至今仍懸而未決的都市問題。
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城市街道。著名城市研究者雅各布斯曾研究發現,在美國,熱鬧、繁忙的街道為應對盜竊、襲擊等問題提供了盡可能的安全之地。不同于傳統認知中對街道避之不及,她發現,沒有街道的地方反而更容易滋生犯罪,而安全的街道,常常是多元、復雜的、混合的。高密度的異質性讓街道擁有一個互相關聯、非正式網絡來維持秩序。
盡管如此,讓街道“更有秩序”的努力也一直存在。
列斐伏爾發現,自奧斯曼對巴黎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開始,一種代表國家秩序的網格式規劃被納入其中。他們嘗試將不同社會群體用道路切割開,讓公和私各成一體。沿著巴黎被工業化與商業化的城市軸線行走,盡管道路不斷擴大,“但除了它們的平庸性,以及它們在意識中服從于壟斷工業外,什么也沒有”。
街道更應縫合而非割裂。在列斐伏爾看來,當勒·柯布西耶推出“新聯合”時,城市生活衰退、荒謬地功能化為“宿舍”,他的問題在于忽略了街道所具有的其他功能,包括信息、象征和游戲功能。“都市生活的所有元素,在別處固定的、冗余的秩序中被凝固的東西,在街道中解放出來,流向它們的中心”。街道的雜亂無章是有生命的,它帶來了信息。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街道也是工業化邏輯的“受害者”。更致命的是,此類“無視都市”的行為甚至影響到城市管理層,并通過其城市治理方式進一步固化。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列斐伏爾以代表整體性、公共性和私人性的三個層級來分解都市經濟和社會結構。他發現,戰略制定者和治理者所在的整體層,傾向于將都市還原為制度化空間,比如道路與公路、都市組織、“自然保護區”等。它傾向于維持腦力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可能性分離,將整體空間分割為區域。為實現整體的同質化,它甚至可能組織不平等的發展過程。
面對強調個人棲居的私人性層次,矛盾“一觸即發”。列斐伏爾發現,通常情況下,矛盾總是出現在整體試圖統治局部之處,普遍性試圖吸收特殊性之時。
這尤為突出體現在“都市規劃”上。列斐伏爾將“都市規劃”視為填塞在工業化和都市化“斷裂”處的“中間物”,它以一種秩序化的形態隱藏和代替都市實體本身。這意味著,它不僅將空間改造成交換而非使用對象,還吞沒了人作為“用戶”和“參與者”等的價值,僅被異化為居住者和空間購買者。由此,都市被工業化邏輯徹底掩蓋起來。
問題是,如何回到“都市化邏輯”上?
從本質上看,都市化邏輯和工業化邏輯的根本性差異,令傳統的認知方式無法真正理解都市。在此基礎上,列斐伏爾提出了一種“都市總問題式”的認識方法,換句話說,都市無法用現存的任何一種專業科學加以分析,它需要一種從總體上介入的“都市戰略”加以重構。
相對應的,從實踐上看,列斐伏爾用“都市社會”來指代在吸收農業、工業城市的基礎上、擺脫工業邏輯的城市形態。與城市不同,都市社會并非是一種已經達成的既有現實,而是“極目遠眺總在實現最前端的那一線閃光的地平線”。
而無論哪個層面,都是對過往城市的一種“顛倒”。
列斐伏爾在書中不止一次出現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在對都市的認知中同樣如此——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都市和都市化過程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上層建筑。但列斐伏爾提出一種相反的假設:工業化可能只是邁向都市化的“一個步驟、一個時機、一個中介和一種工具”。
因為城市的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而工業化的發展則將導向都市化的結果。而在此過程中,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關系也將發生“顛倒”。
列斐伏爾再次梳理歷史發現,都市歷史中有兩個橫貫其中的關鍵性階段。第一個階段,長期占主導地位的農耕經濟變成都市現實的附屬物,起初商業和工業只是促成者,但隨后便成為主導者;第二個階段,主導性的工業將被倒置,成為都市現實的從屬。這個過程已經在發生,但尚未走到臨界點。
在他看來,要實現轉折,重點是在都市三個層次中,私人性層次及其強調的“棲居”,變為本質要素。而這需要代表都市的中間層,即混合層發揮作用。
如何讓都市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盡管列斐伏爾所說的“都市總問題式”的認識方法尚未形成,但根據都市過去的發展規律,已經可以提煉出一些“都市法則”。
一方面,在工業化掩蓋下認清都市本質,并終結“分離”,讓多樣性共存;另一方面,充分發揮都市的作用。這既包括讓都市中常見的習慣性約束方式與現有契約性約束方式并存,也包括將人不僅作為空間的居住者和購買者看待,還包括更加審慎地運用強制性、同質化的空間整體化戰略。
如需轉載請與《每日經濟新聞》報社聯系。
未經《每日經濟新聞》報社授權,嚴禁轉載或鏡像,違者必究。
讀者熱線:4008890008
特別提醒:如果我們使用了您的圖片,請作者與本站聯系索取稿酬。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現在本站,可聯系我們要求撤下您的作品。
歡迎關注每日經濟新聞APP
